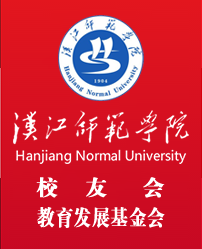1991年暑假结束,父亲陪着我从郧西县天河口镇出发,去远在丹江口的郧阳师专报到。我是那年全镇唯一的大学生。我们乘船沿汉江逆流而上,在郧县将军河转乘绿皮火车到达十堰小花果车站,而后乘公交车到达住在朝阳路的四爹家歇了一晚。次日,我独自带着四爹给的学费乘坐长途客车到达丹江口,一出站就看到接站的学长,倍感温暖。
我在中文系9103班,专业是汉语言文学。1班女生比较多,也漂亮,班主任孙雅萍老师也是一个美女。1班在独立的小教室,我们2、3班合在一间大教室,这让我们很是郁闷——不仅难以拥有风景,连看风景的机会也被无情减弱。我们的班主任是年轻的龚举善老师,教文学概论,才华横溢,文采斐然,讲到文学概念,常常由表入里抽丝剥茧,用“界定”“匡定”“介定”“厘定”“认定”“确定”加以申发,诸如此类。龚老师后来调入中南民族大学,术业大成,现在是博士生导师、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,第四、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。
那时候郧阳地区和十堰市尚未合并,二汽也就是现在的东风公司风头正劲,似乎当时有人把学生分为三类:二汽的,十堰的,地区的。其实他们错了,郧阳师专面向全国招生,省内其他地市的同学比比皆是,外省的也不罕见。有一个女生的家长是二汽的小领导,这个女生欺凌室友,宅心仁厚的系主任于宝成老师一时怒不可遏,晚自习的时候将三个班的学生集中在西二大教室,不点名地用语言向其痛下杀手。我对“风骨”一词的强烈感受由此建立。
我们上学有国家补贴,第一年是26元餐票加粮票,第二年合并为46元餐票,此外还有开水票、洗澡票。男生每月的餐资总是不够用,有些女生却吃不完,她们会把多下的餐票送给心仪的男生,脸厚的男同学则会追着要。其实,餐票在学校是通用货币,无所不能,在学校周边的小超市、录像厅、台球室、苍蝇馆子均畅行无碍。雷勇似乎拿到过很多,我从未享受过这种福利。
1991年冬天,遭遇极寒天气,学校所在的金岗山上水管冻裂停水,消防车每日送水维持生活所需,我们餐后用积雪刷碗,学校似乎还停了几天课。老家的几亩高产桔子树也在这一年冻死,我家失去了一笔稳定收入。我患了肠炎,病守宿舍,与张承志的小说《北方的河》相濡以沫。深沉,悲悯,散发银质的寒冷,生发野火的蓬勃,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生活的迷雾中隐忍前行,他们的人生才因此不致凌空蹈虚。张承志还在《金牧场》的创作谈中说:生命就是希望,它飘荡无定,自由自在,它使人类中总有一支血脉不甘于失败,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。

1992年,数学系毕业的诗人潘能军出版了第二本诗集《一座花园的构成》。我大二,是文学社的诗歌编辑,奉命张罗他在学校的签售会。签售结束,潘老师将剩下的书全部留给了我,我将它们码在床上,旋即被一抢而空。诗集的第一辑是十四行,“精致的美让我走向迷途,雪在你的姿容中显得更加露骨”,翻开诗集,赤裸裸的才华劈头盖脸打过来,令人发指。30年过去,我与老潘成为文联同事,接手他编辑了二十多年的《武当风》杂志,我靠时间而非才华,终于实现了中文系对数学系的“拨乱反正”。
大二上学期,我被推荐去校广播台当编辑,窦唯的黑豹乐队如日中天,《无地自容》响彻大江南北,我让播音员李晓梅在《每周一歌》放了5天。某天中午,饱读诗书的于宝成老师问我播的是什么,我说是摇滚乐。于老师说,我不反对摇滚乐,但你这声音太暴躁了,我说还好吧,他说,教工食堂那边的大喇叭就在我窗户外边。我一想,还真是。抱歉抱歉。
师范院校,音乐是选修课,肖锋老师希望我跟潘云峰一样学二胡,但我坚持选了架子鼓。学校每周五晚上放电影,周六在大礼堂开舞会,门票一元,交谊舞的“扫盲运动”深入到每一个宿舍,大家的热情空前高涨。舞会由老师组成的乐队伴奏,我是学生,当备胎,但鼓手刘老师常常有事。临近毕业的时候,英语系的朱文江对我说,你划不来。我问什么意思,他说,你在上面打了三年鼓,我们在下面抱着女同学跳了三年舞,你说什么意思。我恍然大悟,当场颓废。
喻斌老师那时候三十多岁,儒雅博学,风度翩翩,上课穿着西服,教我们唐宋文学。他主持创研了“古典文学散点教学法”,将文学与史学、美学、音乐、美术、民俗等学科融会贯通,文学鉴赏由此延展成了美学通识课,醍醐灌顶。他的公开课,外系旁听的趋之若鹜,西二大教室汗牛充栋,给我一种中文系被人偷了东西的感觉。喻老师退休后为《十堰周刊》写专栏,李洪领去年将其结集付梓,名《诗书连古今》,在门徒中洛阳纸贵。
学校对学生谈情说爱管得很严,有同学因为牵手拥抱被处分,更有越轨学生被开除,海报墙上甚至写有严禁男女同学在食堂相互喂饭的警告,学生会还有好事之徒每晚组织人去学校后山驱赶那些苦命的鸳鸯。胡赳赳说,1990年代的大学,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诗歌、摇滚和爱情的滋养,那他的青春是残缺的。如此看来,我的青春岂止是残缺,简直是残废。
程明安老师教我们古代汉语,从甲骨文、金文讲起,要命。期末考试,全年级过关的寥寥无几,教室里哀鸿遍野,程老师狡黠一笑,大手一挥:40分算你们及格吧。一时掌声如雷。如今汉江师范学院图书馆楼上“茹古涵今”四字正是程老师手笔,书体不是金文,介于大篆小篆之间,认作“谈古论今”甚或“今福山庄”的人们,应当理解我们当年的悲惨命运。
毕业时大家互留赠言,寝室长肖文才给我们定了一条规矩,无论人在哪里,不论人生际遇,十年后的2004年毕业日必须赶赴十堰最好的宾馆相聚。即将天各一方,那时候我们对这个约定还很悲观,事实上我们很幸运,毕业后能够经常见面,反倒是人到中年以后,大家越来越难以一聚。想起英国作家查尔斯·兰姆的一句话:“童年的朋友,像童年的衣服,长大就穿不上了。”如今大家都已年届天命,很遗憾,也许我们对友谊的努力还是不够。
学校打开水的时间是固定的,每天上午课后,12点左右,去晚了只能临渊羡鱼,老师们很体贴,第四节课常常提前下课。有一次思政课的胡金波老师兴之所至不能自已,忘了我们打开水的事情,大家便敲桌子提醒,胡老师一愣:什么情况?大家理直气壮:打开水。胡老师把粉笔准确投进笔盒,缓缓道:男人喝什么开水啊,喝点自来水不就行了,女生下课!
胡长明是1990级的学长,早一年毕业,在十堰谋得一份营生——这是1990年代初期我们小镇青年的梦想归宿。他说,尚未走出校门的人们都是围墙内的幸福者。我临近毕业的时候,他写来一封信,说他所住的集体宿舍有一个空床,“已置旧被二床于榻侧,可备不时之需。”他现在定居珠海,是攀岩高手,越野达人,卓越的职业经理人。
食堂外面有一个露天小吃摊,一个大铁桶做成的炉子,卖水煎包和青菜面条,有且仅此两样,水煎包两毛钱一个,冬春酸菜粉条,夏秋青菜萝卜。面条三毛钱一碗,不待开锅就下面,开锅之后青菜下锅再煮,开锅之后再点水又煮,如此往复。我们一边骂他奸商,一边饥肠辘辘地眼见着那面条被煮得彻底失去灵魂。
中文系新生报到入学发教材,附加人手一本《文苑精萃》,32开的一个小册子,大约200P,里面收录的皆是先贤杰作,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,《九歌》《离骚》《将近酒》《蜀道难》《三吏》《三别》《满江红》《雨霖铃》,几百篇,说是毕业时由老师随机抽背,不过关的不能毕业。从一年级开始,我们全寝室的人每天嘴里念念有词,有点魔怔,高峰某天突然横在我面前,一声断喝:苏轼,《定风波》!
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是熊欣,17岁,善良端庄,光彩照人,只是身体不好,不能剧烈运动,她毕业第二年因病辞世。不久,一班班长温旭明也车祸身亡。30年过去了,还是会想起他们。
我们《圣风》文学社的指导老师是学校图书馆的杨世泉老师,他经常为我们组织改稿会,拿着我们的作品奔走于各级报刊杂志,极力推荐。我发表于《丹江口报》和十堰文联《新星》杂志的作品都得益于杨老师的奖掖。地市合并前,十堰文联的刊物叫《新星》,地区文联的叫《武当文学》,后来合二为一,就是现在的《武当风》。杨老师的哥哥杨世运那时是市文联副主席兼《新星》主编。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,无论栅栏内的羊群发出过多么欢快的和鸣,但最后都免不了末路亡羊的愁肠。我毕业前夕写过一首诗,《告别金岗山》:“未了的情感 疲倦的飞翔/凉风落日中的梦想/一处一处的心事/被风带走,又被风带走……”我定稿后给一个女同学看,她说,你这哪里是跟学校告别,你写给我的吧?你看,那个年代的我们是多么深情而又笨拙。后来92级留校的胡忠青告诉我,每逢毕业季校广播台都播这首诗,直至学校从丹江口迁至十堰。
丹江口,旧地,我去了几次曾经的母校,车到门口,我跟留守的小哥说,我们是这儿毕业的,过来看看。小哥微笑着打开校门,我递过去一支烟。田园荒芜而又繁茂葱茏,西二大教室,图书馆,大礼堂,琴房,宿舍楼,大操场,依稀旧日情境。1990级的师姐赶过来,晚上带我重走了一遍均州一路、沙陀营路、车站路、丹赵路、大坝路。吃完一碗梦里水乡的炒米粉,往事凌空飞舞,一时浮生如梦。
(本文选自《时光印迹——汉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校友回忆录》)

作者简介
庹明生,1994年毕业于郧阳师专中文系。出版有《无从说起》(作家出版社)、《水调歌头——南水北调中线全纪录》(新星出版社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