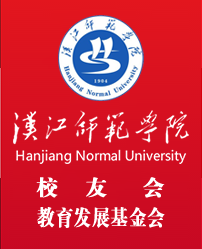二十世纪后几十年间,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,从扫盲到普九,全民受教育程度、适龄儿童入学率迅速提高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,有一特殊群体做出的特殊贡献,最不应该被遗忘,也最容易被遗忘。这一群体共同的名字叫“民办教师”。
“民办教师”早已成了历史名词,可当年在穷乡僻壤、深山荒村,在昏暗的土坯房或破旧的古庙中,正是这些土生土长的、记工分的民办教师,为山里的孩子们点燃了微弱的希望之光。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、《平凡的世界》中的孙少平、《凤凰琴》中的张英子、《一个也不能少》中的魏敏芝,这些艺术人物生动地展示了当年民办教师、代课教师的真实形象。
我在讲台上工作了四十几年,教过小学、中学、大学,最为铭心刻骨的还是初为人师的五年民办教师生涯。和张英子、魏敏芝相比,有比她们幸运的机遇,也有比她们更艰难的处境;有过自豪荣耀,也有过灰心沮丧。四十多年过去了,一些场景仍历历在目,现回忆几个片段,希望今天的人们记住特殊年代里这一特殊的群体。
初入乡校
我担任民办教师任教的地方,是竹山县北乡的邓家河。撤区并社之前七十多里的全流域为一个公社。七个生产大队顺河排列,越往上游山越大、林越深、人越少。公社所在地位于邓家河中段,几十户人家,有一卫生所,合作社(商店),还有一所完全小学。混乱局面结束后,学校恢复正常秩序,为补齐因流失而缺额的教师队伍,父母带着我们举家迁到了邓家河。我得以在这小学戴帽的初中班混了两年,到一九七一年就算失学待业了。
暑假刚结束,管文教的公社副主任到我家,通知我说领导决定,安排我到青松大队小学担任民办教师。反正我也没事干,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,第二天挑着行李就上任了。
我任教的小学距公社所在地三十多里,是邓家河源头处最后的一个大队。这里盖房子有的是木料,做饭有的是干柴,烤火有的是木炭,就是缺少断文识字的文化人。一所小学,总共五十几个孩子,分一二三个年级,四年级就转到公社中心学校寄宿了。一老一少两个老师,年轻的田老师曾在镇上初中念了一年,就被公社叫回来当了民办教师,这次报名参军入伍后,再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了,所以公社就盯上了我。
小学建在大队仓库边上,三间瓦房,中间的隔成前后两个半间,前面摆两张桌子办公,后面支两张床是卧室。东边一间前面两排课桌,后面是灶、厨柜、案板。可一边上课一边做饭,西边一间是一、二年级教室,左边一年级,右边二年级,这种复式班教学在山里很普遍。
学校的那位老教师碰巧和我同姓,按辈分是长辈,过去上过私塾,教语文还可对付,复杂一点的算术题就显得力不从心。他很关照我,让我接三年级,并负责挑水、砍柴、种菜,他负责做饭。我把每月四元钱的津贴交给他,别的油盐、办公用品、点灯的煤油都由他操心。

密林中的歌声
开学没几天,我就发现这大山里的孩子知识少得可怜,大多从没走出过邓家河。课本上的图案,他们分不出哪是汽车,哪是拖拉机,轮船他们说是两头尖的房子,高压线铁塔他们说是长木耳的架子。我和老喻老师商量,要把副课和课外活动搞起来,团结紧张,严肃活泼,要把活泼补上。老喻老师表示支持,只是一个条件,他对这一窍不通,插不上手,一切由我去摆弄。
第一次上音乐课,我把三个年级集中在一起,分男女生两个部分,我先用竹笛吹奏了一曲《颂歌一曲唱韶山》,孩子们个个张大嘴巴,眼睛眨都不眨,完全听入了迷。一曲结束,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,这时我开始讲话,告诉大家,如果好听应该鼓掌,是礼节、是谢意。然后我又吹了一曲,这次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在仓库里剥桐籽的妇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,都跑到窗口门边来看热闹,她们也没见过这样的课堂。我教的第一支歌是《提篮小卖拾煤渣》,光讲唱段的背景足足用了半节课,先介绍了《红灯记》的大致情节,然后一句一句讲唱词。“担水劈柴”大家都懂,纷纷举手,表示自己担过水或劈过柴。“提篮小卖”就有些困惑了,他们提篮摘过菜,打过猪草,就是不知小卖是啥。“拾煤渣”就更糊涂了,大家不但没见过,听都没听过“煤渣”是什么东西。一个星期趁热打铁上了三次音乐课,终于学会了这一唱段。我把自己在小学合唱队里学的一套搬出来,又是大合唱,又是分男女声齐唱,还让几个唱得好的搞独唱。孩子们又新鲜又兴奋,扯起喉咙乐此不疲,下课进厕所,嘴里还在哼哼叽叽个不停。
我搞的第一个新名堂就是编路队,放学时先集合,按生产队来排队,每队选出路队长,举着写有编号的小红旗站在排头,口令一发出,各队按顺序鱼贯而出,整整齐齐行进在田间小路上。队伍一走进树林,各队争先恐后地吼起《提篮小卖拾煤渣》,把林中的鸟吓得扑棱棱乱飞。
吃晚饭的时候,从县里来的医疗小分队一行四人来到学校,说要会会新来的老师,老喻老师迎上前去,问他们怎么知道新老师来了,队长李医生说,他们进山半年了,第一次听到了放学的孩子唱歌,就猜测定是来了新老师,便想见见聊聊天。正好我提着热水瓶来给客人泡茶,老喻老师手一指我:“就是他,我侄儿。”李医生一脸的失望,口中喃喃念叨:“怎么是个小娃子。”我笑笑说:“不小了,满十六岁了。”李医生他们勉励了我一番,说刚一来就有了新气象,好好干。还说山里缺文化人,好多工作都开展不起来。本来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建一个合作医疗室,培养一个赤脚医生,到现在也没完成任务。从那天起,深山密林里不时传出孩子们稚嫩的歌声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《太阳出来照四方》《雄伟的井冈山》就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宝典。
吸人眼球的墙报
开学两周了,一天老喻老师和我商量,再过两周是国庆节放假,他要去看一个亲戚,来回得四五天,叫我在学校顶几天。这一下提醒了我,顺便讲了我的想法,要以学校名义办一期庆国庆的墙报,需要花几块钱,采购点纸张颜料。他毫不犹豫,满口答应。为难的是,我要的东西,公社小卖部没有,须到区政府所在地才买得到。一百二十多里,没有公路全靠两腿走,怕弄不回来。我们正在苦苦琢磨,区邮电所老任一步跨了进来,真是天赐良机。
邮递员老任负责跑邓家河这条邮路,一周一趟,平时只到公社就行了。我们学校这里既没订报纸,也少有书信、汇款,所以给他省了三十里路。这次是刚刚参军的田老师寄回了报平安的家信,信封上盖着“军邮”的邮戳,他这才光临学校,托我们代为转交。
我灵机一动,见缝插针,请他代购文化用品,也就是笔墨纸张。反正也不重,他应承下来。交换的条件是,以后这个大队的邮件除了汇款,其他直接送到学校,由我们帮忙分送,免得他再去钻沟沟岔岔。最后还特别加上一条,我们托他带的东西,如没有邮件要送,他就给我们放在中心小学自己去取。这好办,我说你交给我母亲就行了,她会找五年级寄宿生星期六回家的时候给捎上来。
果然,一星期后我要的材料如数送到。有彩色蜡笺纸,有红黄蓝三瓶广告颜料,还有二十几张大白纸。我迅速行动起来,找资料、搞设计、分配任务。上小学时,美术老师教了一些绘画基础,特别是用比例尺放大图案的技法非常实用,我带的一本《墙报图案手册》这下派上了用场。我选了一幅大气的“天安门上红旗飘”做报头,另外选出“南湖红船”“韶山青松”“井冈翠竹”“遵义灯光”“延河宝塔”等十来幅简单的图片让部分学生临摹,选出可观的备用。又挑选了一批字迹工整的学生抄写儿歌、诗词,都署上姓名。墙报的花边用红纸裁出巴掌宽的长条,剪出灯笼、万年青、梅花等不同花形,用黄色纸衬在背面。老喻老师私塾出身,毛笔字有一定功底,他中规中矩地写了“国庆专刊”四个大字,还抄写了一首毛主席词《满江红》。九月三十号下午,全校像过喜事一样,端的端糨糊,扶的扶梯子,把花花绿绿的墙报贴到大队仓库的墙上。大家远处看看,近处瞅瞅,怎么都看不够。特别是有自己作品入选的二十几个孩子,比过年还高兴。站在自己的作品下面久久舍不得离开,商量着回去告诉家长,要家长前来分享他们的喜悦。
第二天生产队也放假了,仓库门前因为有了墙报,显得格外热闹。大队、生产队的干部,几十个家长陪着孩子齐聚在墙报前,或听孩子们念诗歌,或认真端详孩子们画的画,许多不识字的家长,叫孩子指哪几个字是他的名字。有一个家长在孩子的名字上来回抚摸,小家伙赶紧制止,生怕把这几字抹坏了。大队长也叫了起来,说这好看的墙报肯定费了不少工,谁也不准扯,谁搞坏了扣他工分。几个干部在学校一直聊到中午,见老喻老师不在,就把我拉到大队长家,炒了野猪肉,还硬灌了我几杯酒。
国庆节一过,公社副主任和中心学校刘校长一起来校,听了我的课,还找干部问了情况,又走访了几位家长。大家把我夸成了一朵花,刘校长非常得意,反复说自己眼光很准,推荐的人错不了。我这才知道是刘校长举荐的我,公社副主任表扬了我一番,要我安下心来好好干,明年发展我入团。我连忙回话说,我是临时来顶班的,商品粮的户口还在城镇上,到时候还要上山下乡。他哈哈大笑说:“你这就在高山顶上,除了上天,还往哪儿上?过一段把你户口迁来不就行了。你只管教书,别的不用操心,学区只要有了招工指标,第一个就是你。”当着大家的面,他给我画了个大饼。我当时也挺感动,暗下决心要干出个名堂来。
稻田里的体育课
我和学生们聊天,问他们平时玩些什么游戏,回答让我很吃惊。山里的孩子们会干很多活儿,唯独不会玩游戏。山里人家住的分散,有的只隔一条沟,双方可相互喊话,可要走到一起,非得一两个时辰不可。孩子们很少有机会聚在一块儿玩游戏。到学校后,老师没组织过,他们只会一窝蜂似的乱跑乱追。勉强可算是游戏的就是“斗鸡”,一只腿蜷起,双手抱住,另一只腿跳跃,以膝盖相撞。
我介绍了少年儿童玩的各种游戏,他们听得津津有味,恨不得马上尝试一番。我想好了方案,从玩游戏入手,将体育课和课外活动结合在一起,把学校的体育运动开展起来。
第一招是学做广播体操,当年全国各地都推广广播体操,机关、工厂都搞得热火朝天。高音喇叭一响,大家都从办公室、车间跑到空地上,随着音乐和口令,伸胳膊伸腿舞扎一番。山里不通公路、不通电,有线广播也没牵进来。别说收音机、电影没看过,根本不知广播体操是啥名堂。我对作息时间表作了调整,早自习前安排了半小时的早操,老喻老师特别支持,主动提出维持秩序、带头学操。
头一次上早操,我把托老任买的哨子吹得震耳欲聋,山谷里传出串串回音。上早工的社员都围在场边,看我们又耍啥新花样。分班站好队,我在台子上开始示范。第一节伸展运动,喊一声比画一下,然后叫孩子们跟我一起做。开始孩子们扭扭捏捏,你扯我一下,我推你一把,笑成一团。老喻老师把闹得最凶的揪出来罚站,秩序才稳定下来。小孩记性好,模仿能力强,一节八个动作,一会儿就拿下了。巩固练习时,我让学生一排一排轮流上来观摩。整齐的队伍、整齐的动作、响亮的哨音,让孩子们自信心暴涨,积极性大增。一个星期的操练,广播体操已经弄得有模有样了。
第一次玩游戏,是师生一起玩老鹰捉小鸡,乡里叫“逮羊”,规则一讲大家都懂了。老喻老师当“老鹰”,我是排头,扮演“母鸡”的角色,后面牵了一长串,轮空的学生站在一旁喊“加油”。老喻老师快六十岁了,身子也还矫健,左盘右旋,企图突破防线;我们也左躲右闪,忽东忽西。十分钟结束,他一只“小鸡”也没抓住,一屁股坐到草堆上喘粗气。孩子们也累得四脚拉叉仰躺在土场上大笑不止。看了几场示范表演后,老师退场了,“老鹰”“母鸡”都由学生们扮演了。这一玩就上了瘾,放学路上,孩子们找块空地就闹腾起来。
游戏对少年儿童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,不仅学习人际交往常识,也培养了规则意识和组织能力。我们游戏活动的开展还有了意外收获,几个辍学的孩子哭着闹着要回学校,向家长保证,以后回家多干活儿。首战告捷,我们便不断推出新的游戏种类,孩子们从山上割来几捆十多米长的绵葛藤,一人一根学跳绳,从单人跳发展到双人、五人、七人合跳,还用葛藤编织了一根长藤绳,搞拔河比赛。按年龄、按班级、按生产队,各种形式的分组,花样翻新,孩子们始终兴趣不减。
比较复杂的“找朋友”“抬轿子”“丢包”“铅城门洞”,每天都在学校上演。笑声、歌声、叫喊声此起彼伏,学校成了孩子们幸福的乐园,成了邓家河上游最有生气、最热闹的地方。
寒假时,接公社通知,贯彻“五七”指示精神,第二年举办全公社小学生春季运动会,要求各校都要参赛。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年龄小,而是没有场地训练。平时都是在生产队打晒粮食的土场子上凑合着上体育课,田径赛的正规项目根本无条件开展。参赛虽有困难,也是机会。我直接找到大队长,看他啥态度,愿不愿落后于其他大队。大队长当然不能当落后分子,就问我有啥想法。我大着胆子提要求,把场外边的一块稻田先借给学校作训练场。大队长一愣,随后调侃说:“给你讲个笑话吧。有一次估产,我们依次丈量土地面积,明明是十八块水田,数来数去只有十七块,最后才发现,大队会计的草帽下还藏了一块。大家过年吃顿白米饭,就指望这一头牛都卧不下的几块水田,你拿来蹦蹦跳跳,我可以不说啥,社员们还不骂死你?”我早有对策,告诉他我了解过了,这里水田只能种一季,谷子割后就闲置到第二年插秧。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训练,只在田角上挖个坑练跳高跳远,明年端午节一过,一犁一耙,放水就可以插秧了,不耽误种一季水稻。这一说,书记、队长爽快地答应了,并主动帮我们搞一块跳板和一副跳高的木架子。
春天一开学,地还没化冻,我们就动手了。踩出了一条两米宽的跑道,挖了个三米长的沙坑。但河滩上下尽是鹅卵石,找不到一点细沙铺垫。只好另辟蹊径,带学生上山拢树叶、松树毛,每人一背笼,金黄色的松针松松软软,堆了两尺厚,像沙发一样,比沙坑更安全。参赛队员选定后,正常训练就开始了。山里孩子上大树、爬石崖,像猴子一样灵活,可跳高跳远总是成绩上不去。大队长给我推荐了他邻居家的小姑娘,名叫吴羽,是三年级学生,她上学是十里路,不管刮风下雨,一口气跑到,不出汗、不喘气,长跑没问题。我得寸进尺,和队长打赌:你给买双球鞋,我保证拿个名次。书记也凑热闹,许诺得了奖状他请客喝酒。
校门前一块长长的稻田成了我们的临时操场,收割后的稻茬子被踩得成了一团团的绒毛。给吴羽同学买的一双黄色解放鞋,她从没穿过,每天从书包里拿出来摸一摸、擦一擦,我叫她穿上试跑一下,她怎么也舍不得,说正式比赛时再穿。
五一节,运动会如期举行,我带着十个孩子,举着青松大队小学的牌子走进运动场。我们参加的是低年级组别,所以占了点便宜,因为高山区孩子上学晚,上十岁了才读一年级的比比皆是。吴羽一人报了400米、800米、1000米三个项目。她不负众望,光着脚丫子夺了一个第一名,两个第二名。我派人先一步回去报信,等我们回校时,书记、队长和几个干部跑了五里路迎接我们。这时吴羽才拿出新鞋穿上,她悄悄告诉我,要是拿不到名次就把鞋子还给大队长。大队长手捧着几张奖状,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,说自从五八年大办钢铁后,再也没看到过奖状了。
第二年,要灌水整田了,队长问我这个坑怎么办,我划了一根火柴,坑中松针、树叶燃起熊熊大火,孩子们眼里泪光闪闪。大队书记赶紧安慰大家,说稻谷一割,马上还你们运动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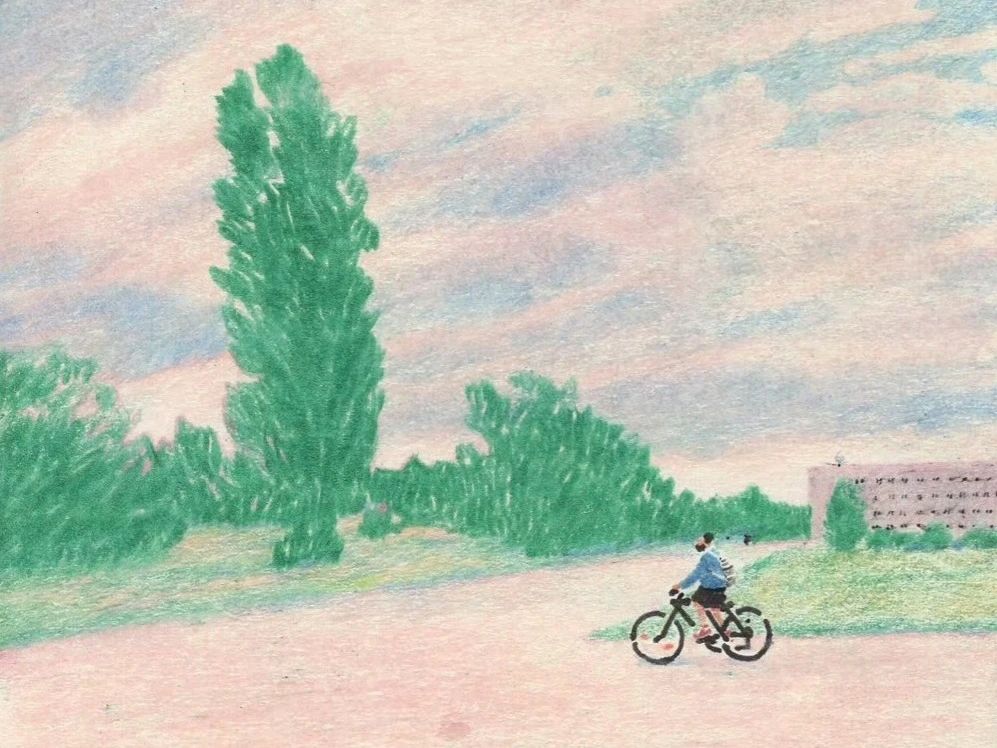
书信开辟第二课堂
根据孩子们少见少闻的先天不足,我想了很多办法来开拓他们的视野。我自己知识也有限,数理化几乎是空白,也没有能力带孩子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别说是县城,就是到镇上看看汽车、电灯都办不到。能做的就是讲故事,以此来扩充知识容量和开发想象力。
开始的讲故事活动,我提前打招呼,要大家做好准备,在故事会上崭露头角。结果并不理想,除表达能力较差、胆小露怯外,所讲的内容都是从爷爷奶奶嘴里听来的山妖鬼怪的故事,什么猴子偷南瓜呀、皮狐子精缠人啦。像牛郎织女、三打白骨精这些故事都没听过。那年月大搞破四旧,我只能选一些保险的红色故事来宣讲。每周来一次故事会,讲过《鸡毛信》《小英雄雨来》《小兵张嘎》,也讲过《神笔马良》《渔盆的故事》,都是些适合儿童接受的作品。讲故事中间,穿插些时代背景和社会知识,诸如电灯、电报、火车、轮船,中国、外国,地球、月亮等,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时间一长,自己肚里也没什么货了,就讲《林海雪原》《奇袭白虎团》《平原游击队》,那时我看的小说也不少,像《烈火金刚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《红日》等,但怕出问题,不敢乱讲。
讲故事时,我发现孩子们的空间概念建立不起来,除了眼前大山,山背后是怎样的天地他们一概不知。“海洋、沙漠、草原、城市”这字都会写会认,就是不知道是啥模样。还是老任送来的邮件启发了我,我将田老师从新疆部队寄来的信送到田家,老伯请我念了信,又替他回了信,看到那张二寸的照片想了个点子。我也给田老师写了封信附在一起,请他一起帮学生开眼界。
田老师对他的学生很有感情,很快就按我们的约定回了信,附上一张戎装照。放学集合时,我念了田老师给同学们的信,传看了照片,特别介绍这封信从数千里外而来,搭飞机、乘火车、路上走了十几天,过沙漠、穿草原、跨黄河,才到了我们手上,大家想想这天地有多大。要求每人想几句话,写好寄给田老师。孩子们很高兴,有人说田老师穿军装真好看,有人说田老师长胖了,有人问田老师拿过真枪没?有人问是骑马好玩还是骑牛好玩。田老师每次回信都讲一点新奇事,什么葡萄沟啦,坎儿井啦,火焰山啦。有张照片上还出现了骆驼,可把孩子们惊呆了,怎么有这样怪的大家伙?一年多的时间,广阔的天地、奇妙的自然,一点点延伸着孩子们的目光。他们的想法也丰富起来,问题也多了起来,有好多问题我也答不出来,比喻有人问田老师的像怎么弄到纸片上去的。我当时没学过物理、化学,自然答不上来。虽然丢了面子,心里却挺高兴,这探寻未知领域的好奇心,正是我希望看到的效果。
我和田老师千里联手,共同的努力,学生们欢迎,家长们也赞同,唯一发牢骚的就是邮递员老任,他抱怨每个月都要多跑三十里路。我开玩笑说,等田老师探亲回来,叫他赔你一双解放鞋。
一九七二年秋季开学,听公社武装部长说,国庆节要慰问军属,准备到田老师家挂光荣军属牌。我要求带学生参加,领导们都赞成。于是大家就忙碌起来,我们准备了几个文艺节目,学生听说到田老师家表演,个个劲头十足。
慰问那天,公社武装部长带队,大队干部、学校师生敲锣打鼓进了田家院子。贴上对联、挂好牌子、放罢鞭炮后,众人围成一圈,田老师的父母坐在门前,孩子们开始表演节目。我们编排的有对口词、快板,还有表演唱,孩子们略显笨拙的歌舞,使大家情绪高涨,特别是撵热闹的学生家长,学着样拼命鼓掌。
我把田老师和学生们的通信选了几段,搞了个“书信朗诵”,两位老人家听得直流眼泪。武装部长最后讲话,赞扬田老师关心下一代成长的举动,也表扬学校的系列活动,说这是拥军优属的实际行动,并安排给部队写封信,以武装部名义感谢田老师心系家乡的事迹。
这种以书信为载体、以师生情为纽带,帮孩子们扩展视野的做法,本是困难条件下的权宜之计,没想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,这应该是为孩子们开辟的第二课堂,只不过当年还没有这个名词,也没有这样的理性认识。通过书信,我和田老师成了未见过面的朋友,我们保持了几年的书信联系,直到我离开邓家河。
作者简介:喻斌,湖北竹山县人,汉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。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地方文史研究。出版、参撰学术著作十余部,发表论文五十余篇。曾任十堰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