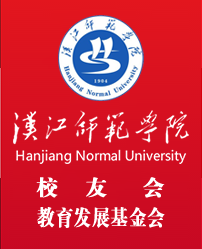母亲从教几十年,从地域上看,始终在竹山的城关、官渡、溢水、麻家渡、双桂、东川、邓家河方圆百里之内兜圈子,供职过的学校有十来所。不论是在热闹的集镇,还是人口稀少的山村,总能受到好评、受到大家的喜爱。究其原因,除心地善良外,多才多艺也是受人尊敬的重要原因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山区文化事业不发达,能断文识字就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了,要是再有一两手过人的技艺,那影响力就更大了。
一
母亲在文艺方面的特长是比较突出的,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爱好者。不管在哪个学校,她都主动要求代音乐课,在根本见不到音乐专业人才的山区,母亲的音乐素养就显得出类拔萃了。只要报纸、刊物上登出了新歌,她总能一手按着乐谱,一手打着拍子,顺畅地把歌词唱出来。广播里播放的“每周一歌”,她也是一边听,一边用笔记本记谱记词。她所在的学校教唱新歌,总比相邻的学校早一两周,不时有其他老师听到学生新歌后,跑来找她要歌单。
1961年,电影《刘三姐》风靡全国,电影里的插曲是让人百听不厌。为了早日在音乐课上教唱《刘三姐》插曲,母亲约上两个青年老师步行二十多里,到宝丰电影院去现场记录。他们买了前后两场的票,第一场一个老师用电筒照亮,一个老师记歌词,母亲记歌谱。放第二遍时,就再校对一遍,深夜两点多才回学校,第二天音乐课“山歌好比春江水”,“只有山歌敬亲人”的歌声就在教室里唱起了。这点本领可让许多人佩服得不行,她却说哼这山歌小调,只是小把戏,当年粉墨登场,唱起西皮、二黄,那才过瘾呢。
1986年,母亲在官渡学校的老同事贺显达老师在我家做客时,聊起了当年的往事,这让我知晓母亲年轻时在戏剧舞台上的风采。官渡镇是堵河边一个重要的水码头,虽位于秦巴大山深处,却因水路便利,客商云集,积淀下丰厚的文化内涵,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飞地。这里古称武陵,有学者认为武陵峡就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原型地,靖康之乱时,就有不少文人于此避难。元初、明末,张献忠、太平天国攻占湖北,这里也是避难所。抗战中,这里也汇聚了一些流亡的文人,一时文风大盛,比县城还要热闹。镇上的文化名人张春谷,是资深的戏曲爱好者,私人出资从几个逃亡的戏班子手里购置了全套的舞台设施,几大箱戏服,还有盔甲、靠旗,刀枪剑戟,锣鼓乐器。又把票友召集到一起,经常在镇上和新街的黄州书院排练演出。这个民间团体取名为“春柳社”,张春谷亲自司鼓,徐云兰的京胡拉的如醉如痴,贺显达和我母亲都是社里的积极分子。母亲说她专攻老旦,像《四郎探母》中的佘太君,《甘露寺》中的吴国太,《岳母刺字》中的岳母,都是她的拿手好戏。
土改运动中,戏班为配合政治运动,在当地工作队领导下,演起了现代戏。官渡街剧社排演的新歌剧《刘胡兰》大获成功,还到相邻的乡镇去巡演,一时声名远播。为了营造震撼的舞台效果,导演别出心裁,在刘胡兰英勇就义这场戏中,把铡刀槽里藏上一截木炭,刽子手双手一按,铡刀下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全场爆出一声尖叫,演员就势滚进边幕后。这一效果震动了观众的心灵,大家高呼“为刘胡兰报仇!”母亲在剧中饰演刘母,刑场一场戏,她在幕后长长的一声“胡兰子……”撕心裂肺,喊得观众双泪直流。同时期排演的《白毛女》也誉满山乡。
贺老师说起排演《小二黑结婚》时发生的小插曲,让两人大笑不止。原来在分配角色时,工作队指定母亲饰演剧中的媒婆“三仙姑”,这一下让她为了难。三仙姑是反面人物,导演把当地玩采莲船时老摇婆的表演程式移到三仙姑身上,夸张的出丑搞怪。头戴老婆帽,鬓插一支花,太阳穴贴着黑膏药,耳朵上吊着红辣椒。这还不算,人物一出场,就百般地扭捏作态,特别是一开口就妖里妖气的一声“哎哟喂”,让母亲恶心得直摆头。于是她提出演不好这个角色,天生无喜剧细胞,稍微有一点滑稽逗笑的动作,就拉不了脸来,就是大雅之堂上的京腔,她也只喜欢苍凉低回的程派,而不喜华丽柔媚的梅派。对“三仙姑”这种角色,从心底里反感。工作队先让贺显达老师来做思想工作,又发动剧组的同仁来帮助,竟上纲上线,用阶级立场、政治态度这些大帽子威吓。母亲到排练场试了几次,感情上过不了“怕丑丢人”这一关,干脆直接就撂了挑子,剧组只好找了一位男士来反串。
为这事,母亲挨了领导的批评,也不管“胡兰妈”、“赵二婶”演得如何出色,单凭《小二黑结婚》这一出戏,给扣了个思想不端正、工作不积极的帽子。
在文教战线上,会唱会演会跳的人才可不少,学校的教师一般都是文化宣传活动中的主力军。母亲在文艺方面的爱好和特长,在教师生活中有了充分展示的机会和平台,真正让她受到大家敬佩的,并非舞台上的表现,而是她的书法水平。
二
旧时代的读书人,写好字是基本要求,差不多都能写一笔像模像样的毛笔字,但能够得上书法水平的却不多。竹山县自古就有浓郁的书法文风,能写好字的读书人,一般都会受到尊重。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作为女性,母亲在书法上获得了一定的声誉,实在属于凤毛麟角。
母亲讲过,在竹山能切磋书艺的,解放前有韩世杰老师,解放后有何一善老师。母亲对韩世杰老师评价较高,特别佩服他上地理课时,随手用粉笔画地图,和教科书上相差无几。韩的书法雍容大度,浓浓的书卷气。母亲学书从颜体入手,后帖临钱南园。韩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,女士腕力较弱,宜求字体婉约秀丽,而母亲又是身高清瘦,最好专攻柳体。母亲却认为,她就是喜欢钱南园的苍劲雄浑,才学了这劲健一路,所以书法风格也显瘦硬刚健。当年在竹山,她为商家写过匾牌、店招,润笔费达到一字一块大洋。
和何一善老师同事是在六十年代中期,何老师曾从事过文秘职业,故一笔楷书规范严谨。在那个特殊年代,他们的特长却派不上用场,大的标牌、标语虽到处都是,可都用美术字,先用直尺划出线条,再把中间涂满。字体以黑体、宋体为主,手写的极少见。逢重大活动或节日,要在墙上、电杆上贴红红绿绿的标语,并不要求字写多好,但写字的人要根正苗红,许多有书写基础的人捞不上这差事。有一次,一位老师不小心把标语的字写掉一个,贴出来后惹了大祸,在学习班被“帮助”了一个月才放回家。我母亲和何老师都属于留有“小辫子”的人,所以贸然不敢去涉及。当然也有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,就是写春联,人多量大,照着农历本上现成的词来写,字数固定,一副对联的词,少说也要写上百遍,肯定出不了错。
在东川时,写对联的现场就在学校操场上,大队干部们商量好,一天一个生产队按顺序来,母亲那几年都是从过小年开始,一直写到年三十的早晨。到邓家河后,因路程远,每个生产队都设一个点,把母亲接到队上去写,有时实在人多赶不出来,我也被推上场,第一次为人写对联我只有十四岁。山里农民也不嫌我字迹幼稚,只要红纸上有几个墨疙瘩就行了。
母亲因书法而露脸,是在1985年。她退休后,先住东川,我成家后,就随我到了丹江口市。这年初春,市里要召开一次法制宣传群众大会,会议的筹备、组织及会场布置都由法院负责。那年头没有喷绘、打印这些工艺,会标都是手工制作。到了开会的头一天,万事俱备,就差制作会标了,偏偏会写美术字的同志几天前出差,说是这天回来,可到下班时间了还不见人影。几位领导和专门留下来负责剪贴的女同志都在门厅里等着。到了晚八点,还没有动静,院长急得头上汗都下来了。我爱人当时主管办公室工作,就来问一下,直接手写行不行?院长答道那不更好吗?可到哪儿找能写这样大字的高手哇!我爱人说,你们快准备笔墨纸砚,我去请人。她回来给母亲一说,母亲爽快地答应了,只说几十年没操练,手生得很。到了大厅,大家有些疑惑,母亲和大家都熟悉,知道她是老教师,但不敢相信这老太太,竟敢揽这瓷器活儿。母亲看了看裁好的大红纸,嘱咐把砚台换成大碗,将四支毛笔绑在一起,脱去外套,挽起袖子,拉开架式。深吸一口气,饱蘸浓墨,斗大的颜体楷书跃然纸上。十个大字写完,母亲一头大汗,全场情不自禁鼓起掌来。院长安排食堂加几个菜,再到家里取瓶好酒,要和这身边的老书法家好好喝几杯。第二天散会时,不少人都在打听,会场上那几个大字出自谁手。从那时起,我也迷上了书法,只不过练了几十年,也还没达到母亲的书写水平。
三
在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诸方面,母亲都能来几下,但这并不意味着持家能力的欠缺。在她成长的时代,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封建传统还有一定的市场,对女性的评价标准,除了淑惠贤德,便要“上得了厅堂,下得了厨房”。有了家庭、养育了儿女,作为母亲就得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,母亲灶上灶下,洗涮补连,都还拿得起来。那时收入不高,我们兄妹的四季穿戴,很大一部分都是母亲亲历亲为。常常是晚上备完课,还要在煤油灯下做会儿针线活儿,衣裤鞋帽、拆旧翻新,将大改小,忙个不停。
编织和刺绣是母亲的拿手好戏,不同颜色的毛线,她用几根竹签,左盘右绕,织出各种花色的图案。母亲成家时,为自己织了一件中长的毛线外套,银灰色,后来隔两年拆洗一次,又添线重织,衣服越来越小,颜色却越来越多。我上小学时,就成了我的上衣,红色占了很大的比例。到我女儿上小学时,已缩成毛背心了。女儿高中毕业时,已变成了一双五颜六色的手套。从1954年到二十一世纪初,从毛衣是稀罕物到“鄂尔多斯”“恒源祥”满大街都是,这团毛线伴随我家三代人,成了珍贵的纪念品。
能挑花绣朵,是乡村人对女性长于女红的高度评价,母亲的刺绣手艺,在学习民间艺术的基础上,融进了中国画的一些元素,可谓锦上添花。特别是对色彩层次的处理,使图案有了立体感,虽题材不外乎花鸟虫鱼,可注意了透视关系,就有了一点文人画的意蕴。在新中国刚成立的五十年代初,会绣花并不是普通人家女儿能掌握的,所以母亲的这一技能,就很被人们看重,也成了她和周围群众建立友好关系的桥梁。那时姑娘出嫁,能有一对绣花枕套作陪嫁是很有面子的,母亲待人热情又肯帮忙,还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。村里就有不少姑娘准备嫁妆时找母亲帮助,或学习画图样,或请教配颜色,也有请母亲为之示范或直接代劳的。
母亲回忆说,她在官渡教书时,妇女识字班办得有声有色,绣花手艺就起了大作用。1952年,全国开展了扫盲运动,学校教师自然是骨干力量,翻身农民学文化积极性很高,就是动员广大妇女参加识字班有难度。有人觉得妇女认字学文化没啥用,洗衣做饭又用不上文化,有些大姑娘怕人议论不敢抛头露面。母亲就亲自到农户家里动员,并许诺只要进了她的扫盲识字班,出嫁时送一对亲自绣好的枕套。这还挺灵,吸引了不少女孩子参加学习,虽然不完全是为了绣花枕套,但这一份诚意也足以打动人。
曾经有人问母亲,样样都会来一下,有什么诀窍?母亲说不管什么技能,只要真心学,用心练,没有练不会的。在她工作过的地方,见不到什么专业人才,像她这样就算高水平了。打乒乓球,整个区不管医疗战线还是行政单位,在女性中没有对手;下象棋许多男同志都得败下阵来;珠算、心算,快得不可思议。她的教训是贪多嚼不烂,各项技能做不到精益求精,皆因浅尝辄止,这也是许多人的通病。遗憾的是,我并没有听进母亲的教诲,也学了不少东西,就是没有搞精通哪一门。

作者简介:喻斌,湖北竹山县人,汉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。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地方文史研究。出版、参撰学术著作十余部,发表论文五十余篇。曾任十堰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