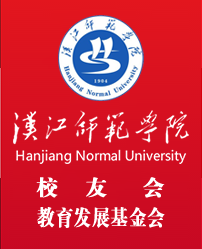从教四十年,从九龙山到新江口,从松滋到东莞,绕了一大圈,又回到了九龙山。一路风雨一路歌,苦辣酸甜,感慨系之。其中,在家乡九龙山学校六年的民办老师生涯,尤其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,常怀心中,挥之不去。
一
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,“四人帮”倒台,毛主席去世。那一年,我十七岁,高中毕业。回乡务农是当时农村学子的必然归宿,庆幸的是,还没毕业我就被安排到大队学校到当民办老师。我兴高采烈,当老师是我从小的理想,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,受人尊重,而且不用下地干农活。那时农村学生特别多,县里推广人民公社“五七教育网”,每个大队有一所小学,每个生产队设有教学点,我被安排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教学点当老师。
高中生在当时的农村可谓稀缺资源,在民办老师中也算是高学历了,但由于文革的缘故,在学校确实没学到什么东西,说腹中空空一点也不为过,好在上面重视老师培训。七月中旬,我怀着喜悦的心情,和同事们一道到杨家河小学参加公社教育组组织的老师培训,学习三算一拼(口算、笔算、心算、汉语拼音)。几百个人在大礼堂集中学习,场面很是壮观。李天翠老师教三算,冉蓉老师教拼音。这两位老师都是当时公社的骨干教师,年轻有为,教学得法。半个月的学习收获颇丰,感觉比我在高中两年学的东西还要多,为我日后的教学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。
我所在的教学点位于九龙山脚下,万家水库上游,生产队打谷场西头。两间土胚房,总共不到三十平方。教室的前方,摆放着一张漏风的讲桌,一块掉漆的木质黑板。几套破旧的课桌凳,都是家长提供的,形式各样,大小不一。十几个学生,其中一年级两个,二年级三个,育红班(学前儿童)五六个,只有我一个老师,所有的课程都由我来上。唯一像样的教具就是一把硕大的算盘,挂在黑板上,教学生加减乘除。三算的特点是从高位算起,属于改革创新的速算法,效果还不错。记得有个学生叫雷正军,上小学二年级,用珠算从一加到一百只需三十五秒,从不失误,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奇迹了,我还向《荆州日报》投稿推介了此事。这个学生后来在大学学财会专业,现在是市委巡察组负责人。每次见到他,我们总是饶有兴致地回忆起当年在学校练珠算的情景。
白天除了上课,有时还要带学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如捡棉花、拾谷穗等。晚上组织队里的基干民兵上夜校,学习时事政治,教唱革命歌曲,排练文艺节目。教室里辟有学习专栏,夜校学员每周都要写学习体会,贴在专栏里相互观摩。教学点成为了当时生产队的文化中心。
二
在教学点工作了一年半之后,我被调到校本部工作。学校除了小学三四五年级之外,还有两个戴帽初中班。我被安排教语文,代全校唱歌课。我把上高中时学过的歌曲教给学生,还教唱一些电影插曲,如《英雄赞歌》《铁道游击队之歌》等。学生们大多喜欢上唱歌课,我在讲台上教唱,有的学生在下面摇头晃脑,乐哉悠哉,我也不批评不处罚,至今仍有学生对那时上唱歌课的欢乐情景记忆犹新。
当时各学校都缺英语老师,学校安排我参加公社组织的英语老师培训班,从最基本的字母和音标学起,边学边教。辅导老师叫邓宗望,是大岩咀中学资深英语老师,水平比较高,据说可以背三千多个英语单词。我们既仰慕又崇拜邓老师,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达到他那样的水平。除了寒暑假集中跟邓老师学习外,我还买了英语磁带以及《英语九百句》等书籍,有空就听录音,不懂就去向邓老师请教。经过一年多的学习,我基本上可以胜任初中英语教学。期末考试,学生的英语成绩也还不错,片区统考,多次获得前几名。
到了1980年,不知何故,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“五七教育网”被撤销了,教学点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小学一二年级回到校本部,这样一来,原来的五间教室就不够用了,于是决定把初中两个班分流出去,办一个初中分部,校址选在原来的大队“农科所”。四间旧瓦房,大队渔场的职工占用了一部分,剩下的给我们当教室和宿舍用。办公桌椅是临时拼凑的,有的还是从周边生产队借来的。我们一共五位老师,承担两个班四十多名学生的教学任务。我代两个班英语课,并担任初中部负责人。除了日常教学之外,老师们自己开荒,种植蔬菜瓜果。没有锅盆碗灶,我们徒步三十多里,到杨林市缸窑厂去买,来回花了一天时间。那时老师的待遇和农民一样记工分,另外每个月有一点生活补贴,最初是三块五,后来涨到十三块。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取消了工分,老师的待遇变为每月二十元。
1981年春节后,正值开学,学校出了一件令人悲痛的事,有个教数学的同事意外身故,课程无法开齐,只好把初二撤了,把学生分流到周边学校就读。剩下四位老师和初一年级二十多名学生。公社教育组领导来巡视,开玩笑说,这是大学编制。到了暑假,初中部正式取消,我们又回到了校本部。自此,大队学校正式告别了办初中的历史。
三
我校师资力量比较强,各科都有优秀的老师,公社组织几次摸底考试,我校总成绩名列前茅。学校的学习氛围很浓,放学后,老师们在办公室里自觉学习,有钻研数理化的,有自学语文和英语的,也有读《中国通史》和毛主席诗词的。每周有两个下午集中研究教材教法,由资深老师当主讲人,对年轻教师进行传帮带。学校定期进行内部考核,对备课、教学和考试成绩实行量化评分,作为调整岗位的重要依据。由于生源减少,教学点逐次合并,加上初中部取消,学校先后两次裁员,主要依据就是考核成绩,实行优胜劣汰。
校长李宪国,是我的小学老师,县二中毕业,文化水平高,领导能力强,很受师生的尊重。我的成长,与当年李校长的培养是分不开的。1978年春,我从教学点来到校本部,李校长安排我当司务长,主管师生的生活,他手把手地教我采购、记账、结算。第二年,学校教导主任辞职,李校长和大队干部商量,让我担任这个职务。为了让我尽快进入角色,李校长言传身教,从课程的设置安排、教研活动的开展、老师们的专业成长和考试命题阅卷各个方面对我进行了悉心指导。他出去开会和参加活动,总是带上我,让我观摩学习,开阔视野。教育组来学校视导,安排我汇报,有一次,教育组长吴远锁老师听了我的汇报,称赞我是公社两个最优秀的教导主任之一。
我有个表叔叫吴夕乾,家住万家水库大坝旁边,早年上过松滋简师,做过几年老师,“文革”中因为家庭成分问题,被辞退回乡务农。表叔能写善谈,性格耿直。他特别喜欢读书人,在我上初中的时候,经常来我家,教我写作文。在他的指导下,我对写作有了兴趣。我当民办老师之后不久,他也被安排到万家柑橘场学校任教,我们的交流更多了。他经常来我家,和我谈写作,谈人生,交流教学心得。他还邀请我到他所在的学校听他的作文课,让我受益匪浅,懂得了要把作文教学和教材以及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,对我日后的作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近几年,我被邀请到珠三角和荆州一些学校做作文教学讲座,总是想起那时候表叔对我的帮助和指导。不幸的是,二十年前表叔患淋巴癌英年早逝,被落实政策、恢复公办老师资格还不到五年。噩耗传来,我泪如泉涌,不仅失去了一位亲人,也失去了我人生中一位可敬的导师和引路人。
四
走出山村,学习更多的知识,是我初入教坛的理想。东风吹来春满园,1977年秋天,受文革冲击中断多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。消息传来,举国欢庆。我和大多数青年一样,跃跃欲试。我报了武汉的几所重点中专。考场设在西斋中学,上千名应届生和社会青年同场竞争,场面甚为壮观。记得当时的作文题是《难忘的一天》,我写了童年的一件趣事,感觉比较顺畅。出场后考生们议论纷纷,都说应该写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内容,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难忘了。我心里也很忐忑,生怕作文打零分。最后结果出来了,团结片区四个大队,共有七名考生上了预选分数线,我是其中之一,并且参加了体检和政审。我踌躇满志,可是天不遂人愿,到了1978年春天,和我一同预选上的三名考生上了学,而我始终没有得到通知书。我叔叔邹时炎时任省教育厅高教处长,我叫我在武汉工作的姐姐去问,说是录取已经结束了,我落选了。我虽然有点失望,但并未消沉,来年再战吧,有的是机会,只要自己不放弃,总有一天会走出山村的。
第二年,高考继续招社会青年,又给了有志青年们一个展翅飞翔的机会。我这次吸取了教训,不再好高骛远,就报了县市几所普通中专。可是又遇到了新问题,增加了一个考试科目——物理化学,各占五十分,加上语文数学,总分为三百分。我的语文数学还可以,物理化学不行,尤其是化学,更是一窍不通。天意弄人,我再一次名落孙山。这次考试对我打击很大,因为高考不再招收社会青年了。
又过了两年,终于传来好消息,师范学校招收民办老师,考政治语文数学三科。我长舒了一口气,只要不考理化,我还是信心的,这次我必须全力以赴,冲出重围。我系统学习了词汇、语法、修辞、逻辑,吃透了初中所有文言文,把初中数学课本上的每一道题做了三遍,用白纸装订的作业本叠起来足有一米高,还把所有的政治复习题答案一字不漏背了下来。每天晚上学习到深夜,夏天蚊子多,我穿上长袖长裤,深筒靴,全副武装。累了困了,擦点风油精。遇到不懂的问题,徒步到几公里外的中学向老师请教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1982年,我再次参加考试,以高于录取分数线十七分的成绩被录取到公安县师范学校。那一年,全县仅招收了二十位民办老师上师范学校。
师范毕业后我在县城关中学任教初中语文,1987年我参加成人高考,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郧阳师专进修,后来去了南方,继续追逐我的教育梦。
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,我也退了休,离开了讲台。时过境迁,可是我对这段民办老师之路仍然历历在目。每次回到家乡,我都要去我曾经工作过的校址看看,追忆那段美好而又难忘的时光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久远的逐梦年代。

作者简介:邹进雄,松滋洈水人,中学语文高级教师,已退休。爱好写作,有作品散见于《少年作家》《洈水》及“东方乐读”等网络平台。